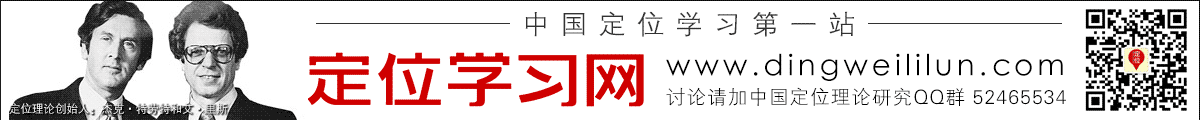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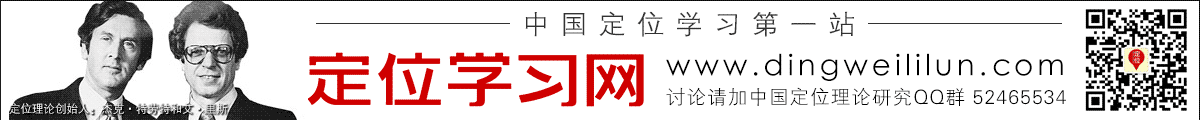
4月1日,北京高层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出现在新华社通稿之中,并被冠以这被称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舆论的氛围来看,雄安新区显然被寄予厚望,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北方经济腾飞的标杆。
不过,雄安新区能否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显然需要经受一系列的考验。
鄙人虽并非经济学家,但无数的事实告诉于我,衡量一个初生城市是否具备新型大城市的潜力,就在于他能否持续长久地吸引企业自发前来投资。只有企业不断前来投资,才会带来就业岗位,只有就业岗位不断增加,才会出现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消费、地产业的真正壮大,一个初生城市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兴盛。即,只有产业的自发的涌入,城市的繁荣才能持续长久。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才能驱使企业和就业不断涌入一个初生城市?究其根本,唯有“超额地域”的利润。
只有该初生城市具备了超出其他地域的“超额地域”利润,才能驱使企业闻利而来,并在该地区“超额地域”利润的帮助下兴旺壮大起来。反之,如果仅仅通过行政命令,调动大量体制企业进入该初生城市,那么这些迁入的企业很可能因丧失地域利润优势而削弱竞争力,从而出现不必要的亏损。整个地区也难以持续吸引企业和就业人口,并在政令冷却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深圳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曹妃甸之所以走向凋敝,其原因不外乎,前者使得迁入的企业能够获得其他地区获得不了的超额地域利润,而后者则与之相反。这样结果的原因,并非源于前者获得了超出后者的政治扶持——毕竟,企业对利润的喜爱和对亏损的恐惧,乃是企业的本性,并不会因政治力量的干涉而改变。
那么,怎样的初生城市才可能具有吸引企业和就业的超额地域利润,并成为未来的商业中心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政治风险、政策优惠以及地理人文等因素。
首先,该地区必须具备相对良好的法治体系。
企业是恐惧风险的,它害怕不可预知,远甚过可见的成本。这决定了某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离不开良好法治下的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没有前者,企业便将面临无休止的刁难和敲诈;没有后者,企业的财富将难以躲避政治风暴的吞噬。这也意味了企业必然会逃离那些缺乏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的地方,并向往法治良俗之所,这是它赖以自存的本能。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上海、天津、香港等大城市(拥有大量西方租界),近代以来之所以能够迅速超越其他内地城市,就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租界有着相对公正有序的法治系统,大量内地商人往往选择将自己的财产迁入租界,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而当时租界内的商业和服务业也逐渐远远优于华区。
从这个角度看,雄安未来的经济前景,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她是否具备相对良好的法治体系。

19世纪后期,天津租界迅速取代了天津老城,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等众多商业设施。东部邻近海河的维多利亚道是一条著名的金融街,集中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金城银行等中外各大银行,以及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等洋行——租界内的房价也远远高于华区。作为北方最大租界所在的城市,当时的天津也成为经济上远超北京的大城市。
一个企业家宁可忍受上海、深圳疯狂的地价成本,也不敢尝试去东北或者山西等地投资,因为他知道诡变无常的官员远比可见的地价更加可怕;而任何谨慎明智的投资者都没有胆量注资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当地狡诈的政府和贪婪的暴民,能够轻易地使他的投资血本无归——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汕头的发展,实际上受制于强大的地方宗族力量。

企业界有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形容东北复杂的投资环境

中国在委内瑞拉投资血本无归(委内瑞拉有强烈的左翼政治传统,政府倾向于借故没收外国投资,以取悦民众,使投资者视之为畏途)

阿根廷华人投资的超市经常被当地人哄抢

受布尔什维克思维影响,现代俄罗斯政府和民众严重缺乏对商业契约的尊重,对合同朝令夕改的态度使得外国投资者恐惧对俄投
其次,该地区需要有对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政策优惠。
企业是逐利而生的组织生物。如果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地域优惠政策或者利益交换,那么企业很难主动迁徙而来,否则即便其迁徙而来,企业在该地区的投入很难持续。因此,地域性独有的重商政策优惠,对于经济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邓小平开辟的深圳经济特区和印度现总理奠定的古吉拉特邦经济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宝石,就在于两者不但在该地区建立了相对良好的法治体系,还建立了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
(深圳经济特区)……第十二条 客商用地……根据不同行业和用途,给予优惠;
第十三条 特区企业进口生产所必需……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或者减免进口税;
第十四条 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相比内地其他极低的税率,特朗普今天的减税目标);
第十六条 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
第十八条 凡来往特区……出入境均简化手续(在国内当时的体制环境下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十条 特区企业雇用的职工……必要时可以解雇,其手续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办理(在国内当时的体制环境下是不可想象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样优惠措施,使得深圳具有了其他任何内地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地域超额利润空间,那些在深圳定居的企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自身的规模不但得以扩大,更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进驻。
从这一点来看,雄安能否超越邓小平的深圳奇迹和莫迪的古吉拉特邦神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雄安能否颁布真正实惠于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地区能否具备地域超额利润,同样还受制于地理政治人文环境。
现代大都市的出现和发展,往往需要便捷的地理环境。香港、武汉(解放前)、广州、天津、上海、重庆、纽约、鹿特丹等现代大城市的出现,实际上得益于其便捷的海运或者水运。
真正的例外是巴西城市巴西利亚,但这座巴西内陆的新首都实际上是一座巴西公务员支撑起来的新城市。
从这个角度来看,雄安的发展前景,实际上受制于能否建立便捷低廉的运输系统。
事实上,很多时候,评估一座城市未来最好的指标,并非政府的政治决心,而是企业家的迁徙方向。因为,作为天生捕捉利润的经济动物,企业家对“地域超额利润”有着得天独厚的嗅觉,他们真金白银的选择,往往比生动的政治口号更加可靠。
而良好的实业投资环境,才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得以兴盛的关键,凡是有利于实业投资的土地,就是发展的希望所在,凡是被实业投资所抛弃的地方,就很难具有未来。这并非自命天才的洞察,是无数事实证明的结果。邓小平的深圳、莫迪的古吉拉特、朴正熙的韩国之所以走向繁荣,工会支配下的底特律、旧体制的东北、查韦斯的委内瑞拉之所以走向衰败,其原因并无二致,皆源于企业家对其的青睐或抛弃。
同样,今天雄安的长远前景,对此亦不能免俗。

“在促使帝国强大和繁荣的所有要素中,没有比提高德国企业盈利能力更重要。”——俾斯麦提倡扩大“德意志关税同盟”时对企业的讲话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强大的奠基人,著名的重商政治家——“国家的繁荣有赖于商业。”

美国的重商传统为其缔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促成了美国的繁荣和强大



关注定位学习网公众号,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