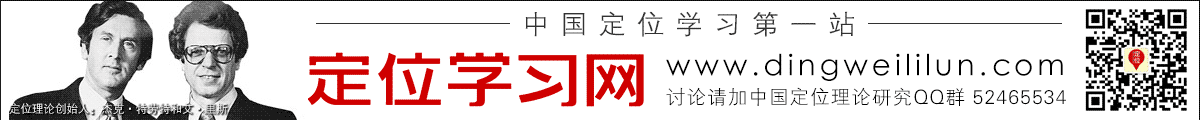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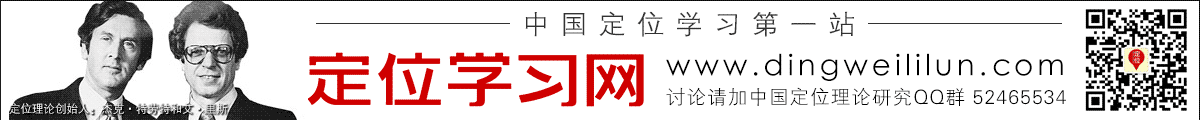
此文是邓德隆先生为刚刚出版的《由巫到礼,释礼归仁》英文版所作序。《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由李泽厚先生著,是一部探讨和解释中国文化源头的书籍。这篇序文经刘再复先生推荐发表在《书屋》2019年2月刊“学界新论”栏目,在此分享给各位读者。

读李泽厚先生的书十多年来,常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李先生著作中散落许多“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语,让我读后掩卷深思,浮想联翩。仅举一例,“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我读到这句话就非常震撼。
先引我与安乐哲先生通信中的一段话:
安先生,您一直以来立志要向西方传播中国哲学,我认为您的使命对世界(不只对中国)很重要。……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可惜学界像您这般有使命又识货的人太少,现在急需将李先生的著作译介出来。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

信中提到李先生消化吸纳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其实远未说全,比如基督教。“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就是消化吸纳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深邃传统,以永恒的宇宙(中国人的“天”,自然山水为其代表符号)代替永恒的上帝,从而将一个世界观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在西方只有另个超验世界才有的神圣性。既然缺乏另个超验的世界,那这个充满了尘俗的一个世界的神圣性从何而来?世俗如何可能神圣?这个世界神圣性的文化资源即是本书《由巫到礼,释礼归仁》所揭示出的巫史传统。即经由周公的由巫到礼、孔子的释礼归仁,巫术中的神明就被理性化保存、落实、行走在这个世界之中。
从而,中国文化中的“天”,既有自然意,又有主宰意,神圣意。这就可以与西方两个世界中的神圣世界(即超验世界)接头。这一接头,就大大强化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悲剧性、深刻度、形上品格。改变、丰富、扩展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相遇时,(这是儒学的第三次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第一次是与墨家、道法家、阴阳家等,第二次是与佛家),能将之包容、消化、吸纳,创造出另一种超越:并不需要神的拐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达至宗教高度,实现心境超脱。使中国文化不止于为鲁迅所痛批的乐陶陶大团圆,而有更高更险的攀登。
李先生说:“使中国人的体验不止于人间,而求更高的超越;使人在无限宇宙和广漠自然面前的卑屈,可以相当于基督徒的面向上帝。”这不但让中国文化在遭遇基督教挑战后重获新生,更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当脑科学发达到能解释,甚至复制宗教经验,从而打破“感性经验的神秘”(参阅James《宗教经验种种》)后,人类向何处去?人类目前的困境,概而言之即挣扎于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的生存状态。是继续异化沉沦于机器的奴隶?(工具机器如手机、网络,社会机器如国家、工作单位),然后再逃离机器做寻求刺激,纵欲的动物?还是像后现代一般陷入虚无?乃至落入被海德格尔彻底掏空“先行到死亡中去”的无底深渊?
来过中国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国人生活的环境,无论居家、办公、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山水画类似于西方的十字架几乎无处不在。其“功能” 即在于助人超脱一己个体的有限、时空、因果,把你带回到大自然当中,脱离俗尘,回归天地,与天合一,实现超脱。尽管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装饰或有意识地附庸风雅,但为什么出奇一致地要用山水画而不是其他什么来装饰,来附庸,可见这恰恰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外化,虽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在这里有对宇宙自然的畏怕,所以人在山水画中非常细小。有畏有怕,才给人以更大的支持解脱力量。
重要的是,人虽细小却不能没有人,人是永恒宇宙的重要部分。这也是来自本书所讲的巫史传统,巫通天后与天合一,是以天大地大人(巫君合一)亦大,永恒的宇宙(天)包含了人,人与物自体的宇宙协同共存,所以天人合一的山水画能让人寻求和实现向永恒宇宙回归。李先生说:“这与上帝造人又逐出乐园再寻求拯救相似,却又迥然不同”。
相似的是,人通过使用制造工具实现从宇宙自然中走出(造人),而在自然的人化之后。人又寻求回归自然山水、宇宙家园(再获“拯救”),即人的自然化。不同的是,不需要另个世界的上帝天国……,不需要入黑暗,受苦难才能得救,而是通由山水画的启悟,获得当下即得,瞬间永恒的奇妙感受。甚至连这奇妙感受也不是必需,只要你在山水画中体悟天地之永恒,人生之短暂,宇宙之无垠,世事之有限,再大事功,再多苦难无非转瞬间的过眼云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
在这里并没有漠视生存的艰辛、生活的艰难,相反正因为生存不易,人世苦辛,才用山水画时时处处予以消解与慰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潜)。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
宋元以降,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这个生活支持与“人生解脱”的功用,但从没有谁这么明确、深刻地将无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更没人将巫史传统资源与两个世界的基督教传统对接,从而升华其悲剧性格与形上品格……。
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不断落败,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使中国文化遭遇“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基督教挑战甚大。从第一代现代知识人(戊戌辛亥一代)的康有为立孔教,到第六代(红卫兵一代)大批名流学者所近年掀起立孔教狂潮,以为缺乏另个超验世界的中国文化不如此就找不到出路。因此,如何消化吸纳基督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能否走进世界、焕发新生、重获自信的时代课题。
与这些学者迥然不同,李先生以另种方式承担起这一时代课题和历史使命。以“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气概与胆识,转化性创造中国巫史传统,提出以亲子血缘情感为本根的“仁”的文化心理结构体和对永恒宇宙即物自体的敬畏,来替代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然还有基督教的圣爱和“永恒的上帝”。通读李先生作品,这一“野心”(消化吸纳基督教)昭然若揭。再举几例。
“宇宙本身就是上帝,就是那神圣性自身,它似乎端居在人间岁月和现实悲欢之上,却又在其中。人是有限的,人有各种过失和罪恶,从而人在情感上总追求归依或超脱。这一归依、超脱就可以是那不可知的宇宙存在的物自体,这就是天,是主,是神。这个神既可以是存在性的对象,也可以是境界性的自由,既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美学享(感)受,也可以是两者的混杂或中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来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论语今读》)
人生艰难,空而责有,纯赖自身努力,以“度”的实践掌握形式力量,实现自然的人化,构成人类生存的起点(这不就是中国一个世界文化的创世纪么!)。同时这美感又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超越宗教,不仅精神超越,理性融化在感性之中,通过“以美启真”实现人的自由直观,“以美储善”实现人的自由意志,“以美立命”实现人的自由享受。人就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真正实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可见美学既是人的起点,又是人的终点(人的自然化),这样美学就超越了伦理学而成了第一哲学。将中国传统的“立于礼”(伦理学)推向“成于乐”(美学)。这不但是李先生对中国思想的继承贡献,更是对世界哲学的普遍贡献。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设定另个精神世界即理式世界以来,经漫长中世纪以人格神上帝具化之,西方两个世界的文化心理结构源远流长,但百年前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今天人们也在大谈哲学的终结。那么,以巫史传统、一个世界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山水画可以与十字架并驾齐驱,到时候了?!李先生说:上帝死了,中国哲学登场。不亦宜乎!此序。
邓德隆
2018年6月 上海

关注定位学习网公众号,更多精彩...
